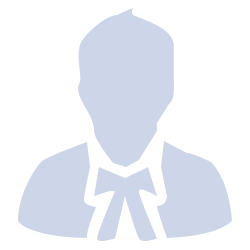配偶一方向第三人借款,由此产生的债务究竟是借款的配偶一方的个人债务还是夫妻双方的共同债务?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存在一定的矛盾,从而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完全不同的判决结果[②]。在这种情况下,厘清并化解婚姻法和司法解释之间的冲突就是司法实践中至关重要的事情。
一、《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基础和司法解释的基石
(一)《婚姻法》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
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有明确的规定,其内容是:“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由此来看,婚姻法把夫妻共同债务界定为“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只有符合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这一特征的债务,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如果该债务的产生和夫妻共同生活根本没有联系,则应当作为配偶一方的个人债务进行处理,比如配偶一方所负的赌债、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高额借贷等。
(二)《婚姻法》和婚姻法解释的效力区分
虽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自2000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并未对司法解释的效力进行界定,但通常认为,最高司法机关进行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81年制定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③]。据此,从制定机关、权力来源等角度来讲,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由最高司法机关制定的司法解释在法律效力上也不可能高于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因此,任何司法解释都要以法律条文本身为依据,任何司法解释都不可能超越所解释的法律条文本身,否则就是无权解释、无效解释。
回到夫妻共同债务的界定问题,由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明确规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才应当共同偿还,才属于理论上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任何针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规定,都不应当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相违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应当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与否的基石,司法实践中只能在该法条限定的范围内进行细化,而不能随意突破或者限制。
二、《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内涵及对比分析
(一)《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内涵
《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就此规定而言:
1、该司法解释确立了“配偶一方举债夫妻共同偿还”的一般原则。
该司法解释把配偶一方所负的债务在一般情况下均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并未考虑该债务的产生是否与夫妻共同生活相关,可以称之为“配偶一方举债夫妻共同偿还”。
2、该司法解释以“但书”的形式对“配偶一方举债夫妻共同偿还”原则作出排除性规定。
该司法解释以“但书”的形式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作出排除性规定,把如下两种情形下发生的债务认定为配偶一方的个人债务:
(1)债权人和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
(2)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即“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所有的财产清偿”。
(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和《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对比分析
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和《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来看,二者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存在如下区别:
1、从规范的角度讲:《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确立了“配偶一方举债夫妻共同偿还”的一般原则,这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是相背反的。
如上所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首先是把夫妻一方所负的债务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然后再看该债务是不是属于两种排除性情形之一,如果不是,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这一法律适用过程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内容是不一致的。《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只是规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才属于理论上所谓的“夫妻共同债务”。进一步来讲,《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确立的是“谁借贷谁偿还”的一般原则,只有在配偶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而负担的债务,才属于应当共同偿还的夫妻共同债务。因此,《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有着本质的区别。
2、从理论的角度讲:《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突破了债权的相对性原则,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则遵循了债权的相对性原则。
债权是相对权,只能在特定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诚如学者所言,“此种仅特定债权人得向特定债务人请求给付的法律关系,学说上称为债权(或债之关系)的相对性……债权为对于特定人之权利,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给付,而不能向债务人以外之人请求给付。”[④]
对于配偶一方的举债行为而言,依照债权的相对性,债权人只能向举债的配偶一方主张权利,而不能向未举债的配偶一方主张权利。据此来看,《婚姻法》第四十一条遵循了债权的相对性原则,而《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与债权的相对性理论相反,明显突破了债权的相对性原则。
虽然在理论上,债权既有相对性,也有涉他性,但凡是存在债权涉他性的,其规范性依据都是法律,而非效力层面较低的司法解释。由此来看,《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对债权的相对性理论的突破,并没有充分的理据来支撑。
三、《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越权及其排除性规定的无效
《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不仅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相冲突,而且加重了未举债的配偶一方的举证责任,导致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保护失衡。具体而言:
(一)《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违反了《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是越权解释、是无效解释。
对《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我们认为:
1、《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相冲突。
如上所述,《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则是笼统的把配偶一方对外所附的债务先界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然后再作出排除性限制,这无疑是对《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背反。此不赘述。
2、《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因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相矛盾而无效。
从《立法法》的精神理解,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要小于所解释的法律本身。由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前提是该债务的产生必须用于夫妻共同生活,而《婚姻法解释(二)》则完全无视该前提,因此是与立法法的精神相违背的,从而该司法解释属于越权解释、无效解释,司法实践中应当限制其适用。
(二)《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排除性规定与人“趋利避害”的天性相冲突,且加重了未借贷的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容易导致法律事实完全背离客观事实,因此是缺乏充分理据的。
1、《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排除性规定与常理不合,且加重了未借贷一方的举证责任,因此基本没有适用的可能性。
(1)趋利避害的天性和情绪性因素可能导致举债的配偶一方有意让未举债的配偶一方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法院判决夫妻离婚的前提是二人之间感情破裂,而在感情破裂的情况下,基于趋利避害的天性,配偶一方对外借款尚未清偿时完全可能有意识地让即将判决离婚的配偶来参与清偿,从而把根本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个人债务通过诉讼的形式“合法”的转变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无疑加重了未借贷的配偶一方的责任。
(2)由于未借贷的配偶一方并未参与借贷过程,故由其举证借贷双方约定为个人债务明显不合常理。
从证据距离角度讲,应当由最接近证据的一方进行举证,而不是相反。未借贷的夫妻一方由于未参与借贷的过程,甚至完全不知道存在借贷这一事实,由其来举证债权人和债务人明确约定该债务为个人债务明显属于举证责任分配不当。
更重要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规定,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债权人作为主张借贷关系在未举债的配偶一方存在的当事人,其应当对未举债的配偶一方应当对债务承担偿还责任的事实进行举证。据此分析,《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明显是把应当由债权人承担的举债责任强加于未借贷的配偶一方,与《民诉法解释》的上述规定相冲突。根据后法优于前法的基本原则,应当确认《民诉法解释》对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定在法律效力上高于《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而不应当再根据《婚姻法解释(二)》来分配举证责任。
综合考虑上述两个方面,借贷的配偶一方有推诿责任的天性驱使,未借贷的配偶一方想反驳又难以举证,从而使得上述排除性规定完全背离了公正的基础,可以纳入“恶法”的范畴。
2、《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排除性规定不合常理,且加重了未借贷一方的举证责任,基本没有适用的可能性。
《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将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作为认定夫妻个人债务的依据从法理上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是,该司法解释把相应的举证责任加在为借贷的夫妻一方身上却缺乏充分的理据,具体而言:
(1)由于未借贷的夫妻一方并未参与借贷过程,故由其举证借贷的相关事实据理不足。
与《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排除性规定的分析类似,由未借贷的夫妻一方举证证实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之间存在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明显加重了与借贷无关的夫妻一方的举证责任,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持,也与常识性判断不符。
(2)根据“谁得利谁举证”的基本原理,应当把举证责任归于债权人一方。
“只要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于己有利的事实主张的,就应当提供证据”。[⑤]由于认定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有利于维护债权人的利益,那么从举证责任分配的合理性角度分析,应该把该事由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债权人,由债权人来举证证实其不知道夫妻双方存在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约定。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离婚诉讼不涉及配偶双方及子女之外的第三人(债权人或者债务人等),因此,债权人无法离婚诉讼中主张由夫妻双方来偿还债务,法院也不宜在离婚诉讼中把某项由配偶一方举债而产生的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综上所述,《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与《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相冲突,且易导致举证责任分配混乱从而严重影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应当谨慎适用。
四、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
在司法实践中的限制性探索
由于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司法人员理解混乱、裁判标准不统一等种种不当适用的情形,地方法院为了统一裁判标准,从而往往限制该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并做出排除性的规定。
(一)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指导意见的形式限制了《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适用。
为了避免司法实践中生搬硬套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从而造成错误判决,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根据司法实践经验,制定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粤高法发[2006]39号,以下简称《广东高院婚姻案指导意见》)。《广东高院婚姻案指导意见》第七条规定:对于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所负的债务,债权人请求案夫妻共同债务处理的,如夫妻一方不能证明该债务已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审判人员根据案件已知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判断同时存在以下情形的,可按个人债务处理:(1)夫妻双方不存在举债的合意且未共同分享该债务带来的利益;(2)该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3)债务形成时,债权人有理由相信该债务不是为债务人的家庭共同利益而设立。
从《广东高院婚姻案指导意见》的上述规定来看,该指导意见无疑遵从了法律优先于司法解释的基本原则,将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的债务——“夫妻双方不存在举债的合意且为共同分享该债务带来的利益”按照个人债务进行处理,而不是一概先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二)湖南长沙中级人民法院的典型判例确认了“为夫妻共同利益”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基本要求。
《人民法院报》在2013年7月4日案例指导栏中刊登的《夫妻共同债务应以“为夫妻共同利益”为前提——湖南长沙中院判决蔡竹清诉梁立红等民间借贷纠纷案》一文中提出:1、将“为夫妻共同利益”作为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逻辑前提,符合婚姻法对夫妻共同债务的实质属性要求,具有充分的适法性。2、将“为夫妻共同利益”作为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逻辑前提,建立在正确的利益衡量基础上,具有充分的正当性。3、将“为夫妻共同利益”作为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逻辑前提,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对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司法的要求,兼顾了善意第三人的正当权益,具有充分的必要性。[⑥]
由此可知,在离婚诉讼及民间借贷等案件中,对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适用绝不能简单化、机械化,应当充分尊重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以“为夫妻共同利益”、“为夫妻共同生活”为前提,结合案件事实,准确认定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五、结语
综合上文分析,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应当切实注意一下几个方面,以准确地认定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
首先,“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有明确的立法基础——《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此后任何针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解释都应当是在尊重《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的基础上进行细化和补充,而不能再沿袭“法外造法”的恶习。
其次,《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规定明显和《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相冲突,且其“但书”条款又加重了未举债的配偶一方的举债责任,从而使得“但书”的排除性规定失去了实际意义,同时《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关于举证责任的分配还和《民诉法解释》第九十一条的规定相冲突,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限制《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适用,法官应当在“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前提下甄别案件具体事实,作出涉案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
最后,“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内涵应当明确:一方面,要求未举债的配偶有举债的合意,至少是明知配偶举债的事实;另一方面,未举债的配偶一方分享了举债带来的利益或者免除了自己应尽的法律义务、道德义务。
[①] 梁传宾:广东奔犇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建党:广东格林律师事务所律师。
[②] 可参考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1)穗天法民二初字第2571号判决书和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穗中法民二终字第1319号判决书。
[③] 198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在该决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赋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就审判工作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进行解释的权力。
[④]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3月第2版,第60页。
[⑤]沈德勇:《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上)》,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3月第1版,第312页。